与世文班真正的缘分需从高三说起。“世界”一词何其浩瀚,“文学”一词何其浪漫,于高三的我眼中,单单“世界文学”这四字,就满溢着无垠的柔情。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语言的高热——至今烧了整三年了。大舌小舌、变位缩音,高考前夕躲在房中悄悄跟读发育26个字母——我至今记得曾因听到一声字正腔圆的“histoire”激动地颤栗。“文学”和“语言”这两个发光的字眼,恰于世文班的培养方案暗合,当时一遍遍翻阅清华的专业手册,目光总在“IWLC”四个字母上粘连得久些。
因并非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高考后先去了新雅书院,大一一年,在对文学的狂热中越陷越深。书桌下边先后藏着《愤怒的葡萄》和《推销员之死》——至于后者如何让我当堂泣不成声,就是失算的事了。所幸前边有学长学姐引路,顺利争取到了来世文班面试的机会。面试的前夜跑到清华学堂109教室门前郑重地鞠了一躬:希望世文班能认我做她的孩子。
世文班认了我做她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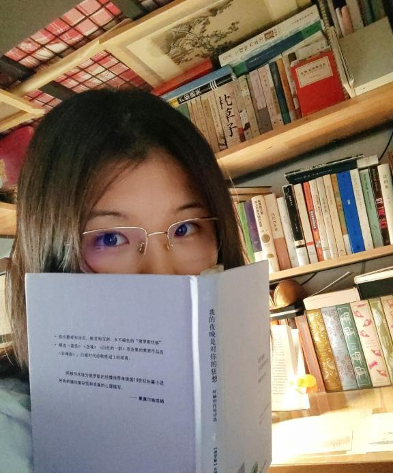
陈诺同学生活照
大言不惭地说来,我好像从没经历过梦中楼阁跌进现实的幻灭,或热恋期被日常蚕食鲸吞的倦怠,世文班没有让我失望过——它比我想象得更好。我尤爱清华学堂109:窗外树老花繁、风动影摇,树影尽数倒映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自成一首短诗。第一个学期在秋季,屋外是秋光如故,屋内是伊利亚特,恍惚间觉得自己在和一百多年前的闻一多学长做同样的事。春天时正巧读Lucretius的On The Nature Of Things,见着园子里的梨花淡白柳深青,就想起Lucretius说每一朵向上怒放的蓓蕾都来自地心挣脱了引力的烈火,深感清华的早春和哲学的文本都满溢着诗情。至今,当我打印出一周的reading assignments,将一沓还烫手的字纸搂在怀中的时候,我的悸动一如那个头一次听到法语的高中生。
上学期开始准备前往牛津的事项,一路至今着实称得上坎坷。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我顽劣地抛掷又随意地弃置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境况中,因此更加用力地将手中书紧攥。我与文学的关系在三年疫情中被我无数次重新定义又再次推翻:此刻,我将它认作人类这个脆弱的物种在病痛和苦难的屠杀下最有力的盟友。近来我甚至觉得,是仅存的盟友。草木无情无心、科学有知无力、神意深不可测、宇宙袖手旁观。但那些歌唱着人性、救赎和爱的故事不知疲倦地向一切证明、向人类自己证明:我们值得被留下,我们值得被拯救,我们残破的、病弱的、污秽的躯体深处埋着星星。不再是书籍在渴求被我阅读:“请君为我侧耳听”,而是我在渴求被书籍拯救:“莫辞更坐弹一曲——”
幸好幸好,文字从不辜负人的。世文班用两年、用lecture和seminar、用数不清的primary 和secondary texts,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据说,看在莫扎特的份上,人们会善待这个世界。看在荷马雨果福楼拜、济慈雪莱狄金森的份上,我原谅这个世界了。


陈诺同学在外文系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中扮演罗密欧的定妆照
也绝非没有过四顾茫然踟蹰不前的时刻。在刚加入世文班时也曾对着发音古怪的陌生术语脚下发软。最怕的还不是需要下的苦功——我更怕,当我的脑海中横陈着各种“主义”、各种批判理论,我还能为《推销员之死》不管不顾地热泪盈眶吗?若将文学认作安身立命之本,若日日夜夜和文字同吃同住,那些曾经扣动心弦的诗行会不会反让心尖摩挲起茧?若识过“乾坤之大”,还有没有眼泪去怜惜草木青?
现在的我明白,人们不仅能够“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且往往是“已识乾坤大,方怜草木青”。
也绝非没有过自我质疑的时刻。我喜欢将文学系的学生比作鸟类学家,案头的书卷即为观鸟镜,我们在纸页的这一侧去追随古今圣贤划过天际线的尾羽。而任何一位敬业的鸟类学家都会在某个时刻对着某书的封底怔怔发问:我怎么就不会飞?世文班教会我的第一课或许是:创作是痛苦的事情,就像分娩是痛苦的事情。难怪古希腊的歌者开篇就要向虚空伸出乞援的手:赐他一首歌吧,赐他一支笔吧,赐他技巧和勇气,赐他冷静和激情。所有那些等待降生的文字,所有那些等待被歌唱的感动,我有没有才情让只言片语能从我的笔尖流出?
我现在已经不再困于这个无解的问题——才华,什么是才华?是无需动心用情也能下笔如神,还是能够比其他人更深、更坚韧、更义无反顾地动心用情?
我认为是后者。
作此文前老师邀我谈谈给学弟学妹们的忠告。即便听上去是陈腔滥调,但我能够给出的建议只有:爱,和爱,还有爱。去爱书。爱一流和三流的作者。爱戏剧和音乐和舞蹈和诗词。
当你爱的时候,你的心就略大于整个宇宙。
若清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世文班该是我在清华的第二故乡。在一个人们随时会感到焦躁脆弱的时代里,世文班为我撑起世界的一个时空,容我“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是我感激不尽的事情。再几周便出发异国,下一个春天不在这里过。但“反认他乡是故乡”也罢,“此心安处是吾乡”也罢,我知道自己会永远在故乡和他乡之间来回,在作者和读者的身份间交互。也许某一个瞬间,我的生活会被拉扯,被撕裂,然后我会发现:裂帛的声音清脆,锯齿的形状极美。而从中醒来、读书、写信的我,与恢弘久远的世文时空同在。
图/文作者:陈诺

